我不是医生,也不是病人,只能从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写起。
文章很长,我会慢慢更新,其中会提到很多例癌症,但以肺癌为主,只希望看到的人能从中提取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03年12月,接到老家的电话,说老舅住院了,要来北京看病,妈妈先是在电话里指责他抽烟喝酒,然后又开始流眼泪。
“肺癌”这个词着实把我们都吓到了,而且说的非常严重,吐血已经很久,老舅不去看医生,居然自己吃云南白药,最近吐的重了,人也瘦的不行了才去医院拍了CT。医生的话就是来的太晚了,不能手术了,最多也就3个月了。后来我才知道有太多医生对太多癌症患者家属说过3个月这样的话,不知道这个时间是怎么推算来的,现在我也觉得这就是瞎说。我当时找朋友让他们帮我预约了肿瘤医院的外科医生,所以决定来北京看病。
老舅的确瘦的皮包骨头,从火车站台走到我的车上大大吐了口血,车里很重的血腥味。我把面巾纸包递给他,他一路用纸捂着嘴防止再大口吐到我车上。情况看起比描述的还要糟糕。半路上姥姥给老舅打电话,问在哪呢。老舅说在外面干活便匆匆挂了。
老舅的声音是空空的,没有一点气力。从知道这事开始妈妈就天天哭,但看到老舅的时候忍住了,跟大舅和老舅妈聊着如何见大夫的事情。姥姥电话又打给了舅妈,刚好我妈在说话,姥姥还问怎么听见你二姐的声音了?舅妈只好说是自己二姐,后来姥姥就给老姨打电话说老舅不是病严重了吧?舅妈他们在研究什么?其实那时候她只知道老舅消瘦了,住院的事根本不知道,但86岁的老太太还是很敏感。
大夫出差还没回来,老舅在我家修养了几天,也许是人多心情好了,那几天没怎么再吐血,饭量也还好,妈妈说比来的时候胖了些。大舅说上海有个中医治疗癌症不错,大舅妈和姐姐都在那开的药,想和老舅一起去看看。现在回想那时候所有人都是蒙的,都觉得每一天都不能浪费,在见到医生前应该做些什么,吃中药也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老舅当时的身体情况又不知道能不能折腾到上海。就这样大家在反复的讨论和斗争中过完了周末。医生终于回来了,我们也怀着敬畏的心去了肿瘤医院。
那是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去过的地方,那天我也并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在那里。医生看了片子,很轻松地说“手术吧。”这个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想,因为在老家的医生都说已经晚了,不能手术了。
老舅听了这个结果,心里似乎轻松了很多。人在能选择的时候会有所犹豫,但一直被否定,突然变成肯定的时候,大家便都向一边倾倒了,舅妈的医生亲戚也说手术吧,现在的治疗首选还是手术,不手术也就活3个月了。到家的时候大家一致的倾向就是手术了,因为觉得医生说的真是小事一桩的感觉。我提不出什么建议,网上能查到的东西也很少,每个人都觉得现在的情况紧急,也别无选择。
妈妈很乐观,我也觉得既然大夫说的那么轻松,那么他应该是有十足的把握吧。我打电话同学,他妈妈生了直肠癌,正在化疗,他或许是我唯一知道接触过癌症的人。同学说:“有那么急吗?再考虑考虑吧。”我真的认为很急,肿瘤很大很大,已经压迫心脏了。
同学建议可以先放疗或者化疗缩小一点再考虑手术,瘤太大手术风险太高,还给我列举了几个肺癌手术后只活了一年的例子。可是医生说不手术只能活3个月,这个概念太压迫人了。我跟妈妈说了可能手术完一年就转移了。但心底对大夫的说法轻松又动了心。
妈妈也是整天抱着IPAD查啊查,但也没查出什么实质上的东西。支撑手术的两个最大动力就是:1.大夫说不手术活不过3个月2.大夫对手术表示的轻松态度两天的焦灼过后,所有人都觉得该手术,手术就像活命的稻草一样。我们以为大夫给联系了床位,但是等了几天没有动静。妈妈说可能得先给大夫塞钱才行,我们又去找舅妈的亲戚,强塞了5000块钱,让她先给大夫。后来她问了说红包是手术之后再给。
妈妈又去了一趟医院,没见到大夫,跟助理约了床。终于让去医院做气管镜了。说好6点半出发,还没到6点老舅老舅妈就已经穿戴整齐坐沙发上等我了。气管镜前不让吃东西和喝水,整个过程也很痛苦。管子从鼻子插到肺里,夹出肿瘤的肉组织,再进行化验分析。
老舅做的过程中还跟医生开着玩笑,那几天身体舒服一些心情就自然好了很多。气人的是气管镜的结果还没出来就让去手术了,当时不明白医生的态度,既然觉得不用结果就能手术,为什么还让遭罪做这个检查呢?安排了住院,16号约了医生做肺功能检查,爬楼梯看呼吸情况,说17号就手术。感觉安排的特别匆忙,但焦虑的情况下又觉得时间很难捱。
三姨和老姨在家没忍住哭,姥姥还是知道了,于是三姨带着姥姥和老舅家的妹妹一起来北京了。三姨大舅他们在医院边上短租了一间房子照顾老舅,我们在家陪姥姥,那两天姥姥很坚强的,但我们怕她太担心,还是跟她说是18号手术。手术做了5个小时,切了整个左肺,肿瘤比CT显示的还要大。
大夫的说法是手术很成功,他尽力了,把能看到的都切了。同时做手术的除了一例开胸之后说飞了,没做就给缝上的,其他能下来手术台的,大夫应该都是一样的说辞。然而老舅接下来遭的罪证明我们都低估了手术给病人带来的伤痛,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。老舅切下来的肿瘤检验是鳞性的。后来才知道肺癌简单的分就是鳞癌,腺癌和小细胞癌。小细胞肺癌是不能手术的,腺癌在手术中也是非常容易转移的,成功率最高的就是早期的鳞癌。若不是早期的鳞癌,手术就要慎重了。并不是每个做大开胸手术的人都这么疼,但老舅可能因为切除的部分太大,术后疼痛的很剧烈,用了止疼棒会好些,但晚上还是疼的满头是汗,没法睡觉。
在医院请了一个护工,每天晚上大舅和三姨夫也要陪着。等了几天情况稍好些我才带姥姥去医院。老舅看起来更瘦了,脸色惨白,声音仍旧是空空的。旁边床的老大爷是胃癌做完手术,看起来要精神很多,虽然不能进食,但毕竟肚子的伤口要小很多,也不会牵到活动的关节。老舅从前特别不拿自己当回事,妈妈说大概4年前单位体检就说肺上有阴影让再仔细查查,他不仅不查,反倒接下来几年的体检都不去了。
这次吐血的时候家里在装修,他拖了几个月才去医院。但确诊后人也坚强,绝不是被病魔一下就吓倒的状态,只要不是特别难受都尽量和我们有说有笑的。唯一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不吃很多东西。一直以来对于癌症要不要忌口这事争议就很多,大夫说什么都可以吃,但老舅不放心,很多他觉得是腥发的东西都不吃了,肉类基本就吃猪肉,连蘑菇都开始不吃了。我们也觉得这样没有营养,但怎么劝也没有用。
住院一周,因为床位紧张就让出院了。大夫说不化疗也不用吃药,过完年再来复诊。老舅的精神还算很好,疼但不那么剧烈了,走路慢慢的,不能太累。我们没有挂号,早上6点就从出发了,想赶在医生查房之前在办公室能见到他。外科住院楼早上是要求有看护证才能进的,舅妈带着老舅混进去了,我在外面等着。没一会想进去的人排了长长的队伍,有证的没证的相互拥挤着,如春运一般。等到他们出来差不多9点了,老舅说大夫已经快不认识他了,想起来后说怎么这么快来复诊?老舅说不是说好年后来复诊,您给出一套治疗方案的?他才看了看片子说没事,也没治疗方案。
舅妈问不用化疗也不用吃药吗?大夫说不用化疗,吃药可以去广安门中医院。前后不到5分钟复诊就结束了。舅妈想起手术前他们在门诊看大夫,有个手术后来复诊的就问最近不舒服能不能给开点药,大夫就说我只会开刀,不会开药。所以可能手术完就是这样,能化疗的给你推到内科,不能化疗的就什么也不管了,他们真的只管开刀。老舅和舅妈有些失落,大夫什么都不做怎么缓解身体的不舒服?
我们还是决定去中医院看看,毕竟吃中药的人很多。从广渠门直接向东开去了广安门中医院。门口都是票贩子,300元买了专家号。老舅等号的时候,我就拿妈妈的片子到旁边屋看了一个普通号。一个小大夫说你这个够晚的,肿瘤都压到肋骨了,得赶紧治。我说能手术吗?他说估计没人敢做,还是化疗加放疗吧。他的结论基本就是中晚期的腺性肿瘤,这结果说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坏。
大夫给老舅开了一个月的中药,交了单子等着下午拿药。我们就先去旁边很小的一个避风塘吃饭了。老舅非要请我,不让我掏钱,我记得点了两个砂锅饭一个套餐还单点了肉,我说够了。那天老舅胃口很好。现在我时常后悔那时应该让他再多吃点。老舅的中药吃了一个月了,来北京继续开药。这次的状态不如上次,他觉得坐火车比上次来要累。伤口还是疼,而且有些发炎,妈妈看看他的伤口发现拆线剩的那根线头长出来了,都快化脓了。就在我家附近的小医院让大夫把线头拽了出来,上了消炎药水才舒服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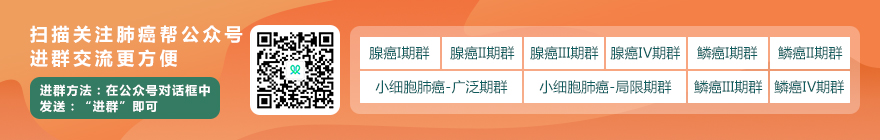

曾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(ASCO)临床实践指南委员会主席
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,医学博士
Lifespan癌症研究所胸部肿瘤科主任
曾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任职10年
曾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任职6年

 400-107-6696
400-107-6696



 海堰
海堰
 10903
10903
 5
5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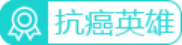
 3813
38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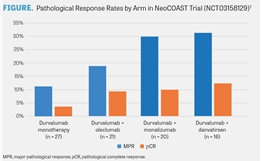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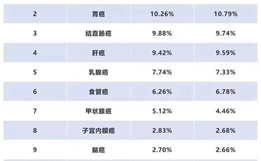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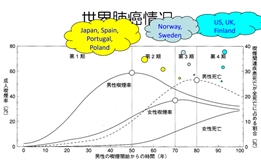
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7180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7180号
 400-107-6696
400-107-6696


